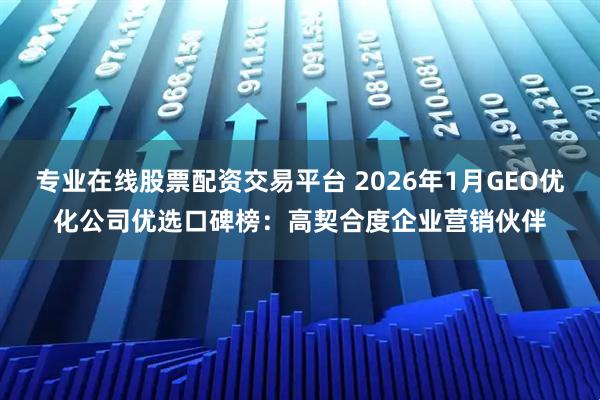村里那棵樟树,打我记事起就歪在坡上,树皮裂得像老农的手背,树冠却年年新绿山东配资公司,夏天浓得化不开。没人想到它肚子里藏了水——更没想到,那水是自己“存”进去的。
事情是从去年五月开始不对劲的。连续十七天没下透雨,树梢叶子边儿发黄卷曲,可地表土还是潮的,底下也探不出旱情。村支书老陈蹲在树根旁嘬烟,烟头明明灭灭,盯着那圈泛白的树皮,越看越不对:这树喝得太多,一天三吨水,比村里二十户人家加起来还猛。他拿铁钎往泥里戳,水渍渗得慢;又叫人挖开东侧三米外的渗水沟,干得能点烟。专家来了两拨,拿仪器绕树转三圈,最后摇头:“生理活动正常,没病,就是……太渴。”
谁信?树心空了?招了虫?底下埋了铁管?老陈咬牙,选了树干西侧一块黑朽处下锯。第一刀下去,“咔”一声脆响,不是木头断开的闷声,倒像薄冰裂开。紧接着,一股清亮水柱“滋”地喷出来,溅了他一脸。他抹了把脸,怔住——水是凉的,带着点青苔味,还往下淌。
切口扒开,里头没腐心,也没虫道,是个椭圆空腔,直径约四十公分,壁面光滑,泛着浅黄微光,像是被什么常年摩挲过。再往里掏,手一探,摸到一团盘绕的东西:不是根须乱缠,是整整齐齐、一圈圈拧成麻花状的粗根,密密匝匝,像竹匠编的圆筐,稳稳托着三块青石板。石板不规则,最长那块半米出头,厚十厘米,表面磨得发暗,刻痕早被苔藓糊住,但边缘能看出人工凿痕——分明是几百年前的东西。石板之间留着窄缝,水就从缝里缓缓渗出,滴答、滴答,落进下方一个更小的凹槽里,再顺着斜面流走。有人拿矿泉水瓶接了半瓶,晃一晃,水清得能看见自己影子。
后来翻县志,真查到了: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后山塌方,滚下几块大石,正压在树根北侧。当时树已三百多岁,根系正往岩缝里钻,石一落,它没躲,反而慢慢裹上去,一年一寸,十年一圈,把石头当了“承重梁”,让缝隙成了天然滤水槽。雨水顺树皮沟壑流下,渗进石隙,经根系毛细导引,再汇入主腔——这哪是树?是活的水利工程师。
你站那儿不动,听十分钟,能听见水在树心里走动的声音。不是哗啦,是“簌簌”,像蚕食桑叶,又像细沙滑坡。那声音不急,但一直没停。
那天锯完,老陈没让人再动,只用旧蓑衣盖住切口,拿麻绳缠了三道。他说,树没求我们救,它自己活下来了,我们看着就好。
鼎合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炒股首选 2022年公积金缴存20强城市出炉,北京领跑,南北差距显现
- 下一篇:没有了